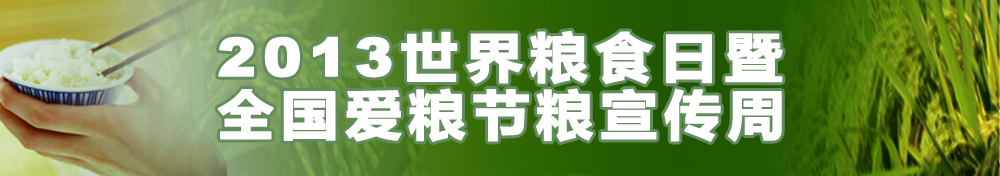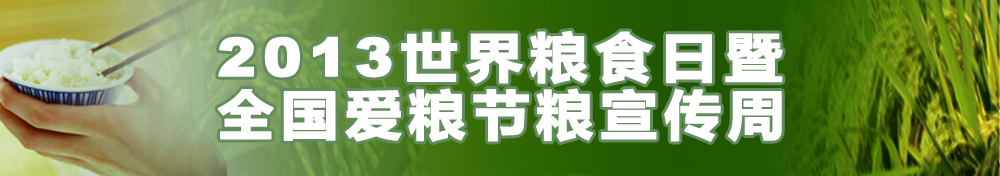于清
提要:孩提时代的我们,对漫山遍野的地瓜情有独钟。因为那是我们填饱肚子的希望,那是全村老小全年的口粮。
我是吃地瓜长大的——或者准确点说,在鲁西南地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吃地瓜长大的。
我的家乡是一个僻静的小山村,四周几乎全是山,只有东面地势稍平,一条蜿蜒的小道通向村外。山腰以上,是茂密的柏树林,郁郁葱葱,苍翠欲滴,像给巍峨的群山戴上了一顶黛青色的帽子。山腰以下,是先辈们用凿过的石块砌起的梯田,里面长着的全是地瓜,夏秋季节,地瓜长起长长的秧子,顺着地堰爬下来,像一架架绿色的瀑布从梯田里溢出,与翠柏交相辉映,形成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
孩提时代的我们,是不大懂游山赏景的,只晓得贪玩填饱肚子,对漫山遍野的地瓜情有独钟。我们眼巴巴地盼着小秧苗快快长大,因为那是我们的希望,那是全村老小全年的口粮。山脚下的洼地里,种着麦子、玉米,那是我们的细粮,指望不上。
一开春,大人们就忙活开了,育苗、整地、翻地瓜沟,直到担着水小心翼翼栽上苗,才能喘口气。
等到地瓜垄上的土有裂纹的时候,说明结了小地瓜。裂缝稍大些,我们这群男孩子便耐不住了。把地瓜偷偷挖出来,在山崖边垒起小灶,架起来烤着吃,一阵狼吞虎咽后,个个儿成了“小包公”。然后,割完草,心满意足,回家。
秋天,天气渐渐转凉,地瓜叶子渐渐变蔫,地瓜垄上裂缝越来越大,像绽放的笑容,此时,也正是全村人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就要收获地瓜了。
每家每户能分到很多很多地瓜,家家户户上顿下顿开始吃地瓜了,煮着、蒸着、烤着……静谧的小山村弥漫起地瓜的香气。
地瓜全身都是宝。
大人们把最次的地瓜运回家,放着当前吃。即使刨坏的地瓜,还有剩下的小头头、小根根,也不舍得丢下。记得母亲把这些边角料剁碎,放在大锅中,加些玉米糁,一起熬,我们这里叫做吃“地瓜黏煮”,特别黏、特别香、特别甜。
最好的地瓜,完整的、顺溜的,要轻拿轻放,担回家存放在五六米深的地窖中,等到来年春天吃。
个头最大的地瓜,切成片,晒成地瓜干,放进粮囤里,这是乡亲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湛蓝的天空下,层层梯田间,山上山下到处是白花花一片,仿佛朵朵白云飘过青山绿树,煞是漂亮。最怕的是阴雨天,秋雨绵绵,眼瞅着好端端雪白的地瓜干发霉变黑,是最心痛的。
长大了,我要去十几里外的镇上求学。母亲将地瓜干磨成面,掺上些玉米面,摊成煎饼。每周末下午,我用木棍背起一大包袱煎饼,步行去上学。每顿饭两个煎饼,加点咸菜,一碗玉米面稀粥。每每此时,便想起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的话:“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比快乐,同伴们常常朗诵起《论语》中的句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981年夏天,乡亲们不知换了什么地瓜品种,绿油油的地瓜田里,居然开出了朵朵小花,蓝莹莹、粉嘟嘟的。就在那一年,我以接近满分的成绩在中考中脱颖而出,取得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当时16岁的我,欣喜之余,深知自己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而今,看着乡亲们餐桌上的主食地瓜变成了副食,小麦这些细粮变成了口粮,鸡蛋、肉、油不再稀缺,少年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感到无比的欣慰!
每每看到地瓜,我总要禁不住细细端详它其貌不扬的外表:粗陋的纹理、矮胖的躯体、傻乎乎的模样,心里便会想起快乐的童年时光,想起那个缺粮的年代……
作者单位:济南市平阴县粮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