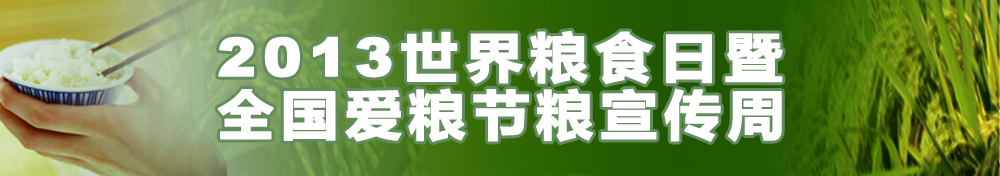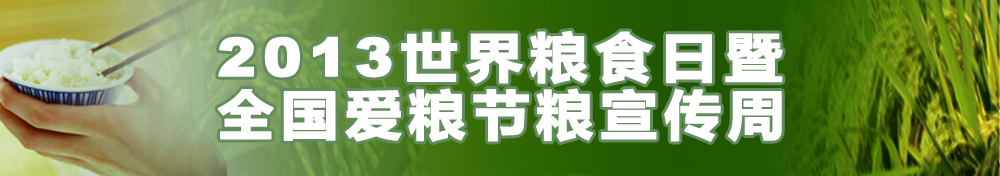刘志
提要: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庄稼人,土地、粮食已融入我生活的点滴,我得像珍爱生命一样珍爱它们……
此行,每人都有抱怨。只是有人不语,有人却又停不下来。可话也就是那几句,反反复复,没什么味道。我依着窗,把整个身体全贴上去,舒服极了。透过不明不暗的淡蓝色玻璃看城外的春景,却丝毫抓不住半缕。
车速不很快,我开始数路边的树。我希望在路的尽头或是树与树之间寻觅到春天追赶我们的脚步,可终于还是失望。快进村了,才切实感到陌生。除了浓厚的土味,余下的都是格格不入。
入村,迎面扑来的便是土。那种不分粗细,强势压人的姿态,逼真得像一首上世纪70年代的老歌,每一股都透过我咽与喉之间纷繁错杂的管,进入我的肺,然后再一股股地退回来。其间,难以数计的细沙、土块、石子也一并进入我的身体,堵在我食道间细小的一段,难以呼吸。
学校除了一座3层的白色小楼,余下的都是黄土和长势惨淡的树。风一过,呼呼的看不见人影。这里的风又不比长城以北,没一股汉子的蛮劲。若真的在北国遇上大风,没半把个月是停不下的。风停,土地变得干净稀寡,像掉了肉。而这里,风刮几日,停几日,就只是卷土。树上,窗口,不管屋里还是墙外,凡是风穿过去的地方都坚持着一层厚厚的土。所以,总盼雨,可雨一来又和成了泥,路都难走几步。
我的学生大多也是土做的,他们挠着总也洗不干净的头发和我一起回忆萧红笔下的鲁迅先生;他们拿出带着土色且携带着天真表情的脸问我艾青诗歌的深刻寓意;他们伸出黑色的伤痕满满的小手拉我的衣袖祈求在试卷上多加几分……
有一次,我讲到美人脸上的痣。大概是因为难以理解,我只好拿田间的坟头搪塞——他们的世界总绕不出村子。之后我又饶有兴趣地一一问了他们家里的田产。使我惊奇的不是他们口中的数字,而是那些脸上无比骄傲的神情。
校园被那些随处可见的小麦、青葱、蒜苗划分成一个个正方或长方的格子,单调的绿色被不分层次地滥用。它们爬上别人的眼角,它们浸过黎明的太阳,它们抹在深夜的月光……课闲的时候,总见老师们插在土里干数不完的活。几时除草,几时浇地,心里都盘算着,生怕落在别人后头,得个好吃懒做的名声。麦苗在霜冻里反青了,青葱也一波赶着一波冒出来。人们的性子更急,等不上壮起来,就在田头拔上几根,顿顿饭离不了口。我也偶尔去土里帮忙,伸伸胳膊,动动腿脚。还不等出汗,就躲了去,听一边的老师讲土里的故事,难得有几段生动的说唱,却总也离不了笑。有时绘声绘色,还不忘搭送几个动作,表情像极了班上的学生。
我又时常想起与学生讲的那些伟大且冠冕堂皇的话,其中常劝慰他们努力学习,逃出去,避开这里的人,这里的土地……那时学生也频频点头,并且发出令人欣慰的誓言。可如今我却再难坦然,更愿意听他们讲关于村里的故事。
在我不断徘徊和彷徨的时候,村里的友人给了我答案:村里的人都是长在黄土地上的庄稼,浑身都带着土味。
这是我一段短短的支教经历,后来,有幸进入粮食系统工作。对土地、对粮食,又近了些。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庄稼人,土地、粮食已融入我生活的点滴,我得像珍爱生命一样珍爱它们。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市粮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