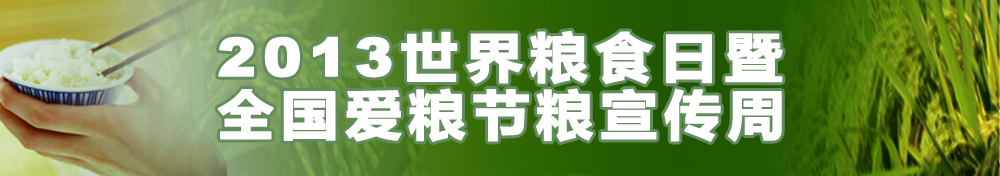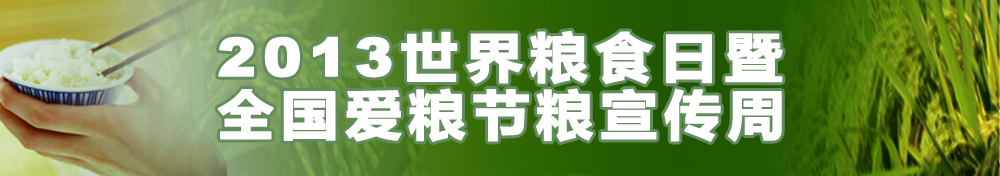秦奋
提要:收获完这一季稻谷,张兆虎老人终于长长舒了口气。他坐在田坎上,解开腰间那条黑黢黢的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反过手去,揉着有些酸胀的腰,好一会儿,还在轻轻地喘气。他似乎就是为种粮而生的,旁人都觉得下田又脏又累,他却觉得挺带劲儿。他曾经饿得抓起路边的青草就往嘴里塞,那印象太深刻了,正因如此,他深深明白粮食是多么可贵。
收获完这一季稻谷,张兆虎老人终于长长舒了口气。他坐在田坎上,解开腰间那条黑黢黢的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反过手去,揉着有些酸胀的腰,好一会儿,还在轻轻地喘气。
“老头子,明年还是别种了吧,都要死的人了,还在逞什么能哦。”来帮他的几个晚辈对他笑着。
“鬼娃儿,别说那些屁话,我这把年龄还能下田,也算是福分哦。”老人伸出右手,在地面狠狠地拍两下,手臂上的肌肉,真的还挺结实。
“不过,真的有些吃不消了,不服老不行呀,明年,明年怎么办呢?”张兆虎有些失落,他的眼前浮现起当年他和伙伴们在田里比赛插秧的情形。如今,那之中有好几个已经去世了,剩下的都已经安享晚年,惟独他,还操持着家门口那4亩稻田。他已经76岁了,头发几乎全白了,背也有些佝偻,脸上的皱纹就像开裂的土地。不过,身子还挺硬朗,说起话来嗓门儿跟敲锣鼓一样洪亮。
算起来,他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就这副天生的好身板儿,给他带来过不少好运。13岁那年,他就开始下田栽秧,居然比两个哥哥还利索,这让他多得了父母的夸赞和喜爱。1957年,刚20岁,他到大队上缴公粮,碰见了邻村的一个姑娘,也就是他现在的老伴李德芬。老太婆回忆当年,眼光发亮:“那会儿他挑着满满两大筐谷子,还有说有笑的,而别人都是累呼呼的样子,就注意上他了。”结婚后,张兆虎接替父亲成了家中的骨干劳动力。那会儿,农村没发展多少副业,除了家里的一小块菜地,人们最主要的活儿就是种稻谷、玉米。张兆虎是远近闻名的劳动能手,基本上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活儿,队长在村民大会上还几次点名表扬过他呢,这让他们一家人都特别有面子。他似乎就是为种粮而生的,旁人都觉得下田又脏又累,他却觉得挺带劲儿。每次,他脱下鞋子,卷起裤腿,趟下凉沁沁、软乎乎的水田,就感觉心里特别踏实。他曾经饿得抓起路边的青草就往嘴里塞,那印象太深刻了,正因如此,他深深明白粮食是多么可贵。
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张兆虎夫妇二人与尚未成家的两个小儿子单独分户,分得4亩水田、6亩旱坡地和一片林子。他变得更有干劲儿了,仿佛那土地就是他的亲人,每次犁田、插秧、薅草、收割,都像在与土地交流,在这种交流中,他看到了一家人的希望,感受到了生活的满足。特别是当稻谷颗粒归仓的时候,他就会情不自禁地一遍遍捧起,仔细端详。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看着木囤子里总是满满实实的谷子,张兆虎觉得心里踏实。后来,两个儿子都成家了,再后来,他们都离开家,到外面做工去了。而张兆虎依然守着自家的土地。1998年,屋后那6亩旱坡地退耕还林了,那时候,他已经年逾花甲,那4亩水田还是他的宝贝。
两个儿子都混得还不错,每年春节回家,都会给父母留下一笔生活费。他们说,都这么大年纪了,是安享晚年的时候了,现在种粮也不划算,还是把地让给别人种,要是觉得没事干,就跟着他们出去,带带孙子。张兆虎理也没理,这4亩稻田,他苦心经营了几十年,不到干不动,他是不会放弃的。
70岁那年,儿女们都回家给他贺寿。那是在5月上旬,坐在家门口的空坝上,看着那片郁郁葱葱的秧苗,他喜滋滋地对坐在身边的小儿子说:“今年天道好,你看,长得比往年都好。”
“好什么呀,你还这样种下去,别人会说我们不孝顺呢!”小儿子借机委婉劝他。
“关别人屁事,我这样才过得舒坦,我们农村人,哪有不种粮的!都像你们去打工,粮食都不种了,大家吃什么?”他顿了顿,又冒出一句:“要不然你们回来种。”
被父亲这么呛一句,儿子哪还好说什么。就这样,这个古稀老人还是一年一年,经营着他的4亩稻田,为他种的水稻高兴着,忧伤着,付出着,也收获着。
不过这两年,他真的觉得快要干不动了。每下一次田,身子就感觉困乏得不行,有时得休整两三天才能恢复。他有点惆怅,有点不服,但又能怎样呢。
“老头子,在想啥子哦,你看你今年的穗子,可不比前些年哦,那些草也懒得薅了吧。”又有人冲他喊道,坐在田坎上走神的张兆虎愣了一下,他的心里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愧疚感。
是呀,是比不上前些年了。明年,明年还种吗?明年谁来种呢?他缓缓地站起身,默默地向家中走去……
作者单位:四川省筠连县粮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