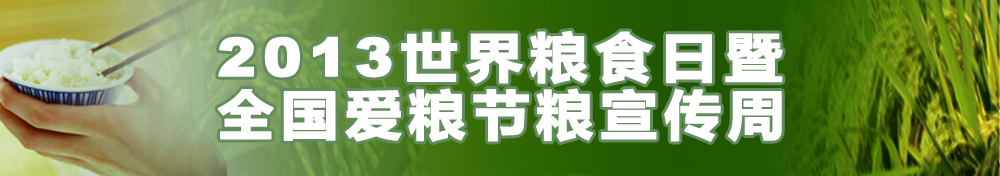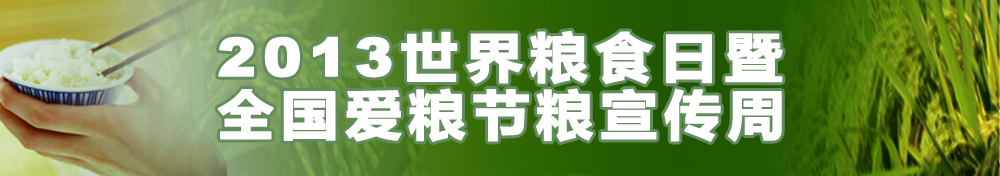朱晓平
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而在我,却是一张薄薄的粮票。
有些年龄的人对于粮票应该不会陌生,在粮食短缺的年代,到粮站买米,仅仅用钱是买不到粮食的。而且推而广之,就连粮食复制品、油条大饼、面条包子、糕点饼干,等等等等,反正一切米字旁、麦字旁和食字旁的食品,不但需要钞票,而且还要粮票。一碗馄饨,半两;一个烧饼,一两;一碗片儿川,二两半。加起来的数字,刚巧应了一句乘法口诀:二二得四。
记得参加工作不久,毛头小伙儿一个,一个人到金华出差,毛毛糙糙竟然忘带了粮票。那时候外出联系工作,对方单位绝对不可能有酒饭招待,事情办毕,起身握手,就算是不错的礼遇了。至于当时官差如何接待,倒也没有认真地进行过研究。签完合同告辞出来,时近中午,饥肠虽未辘辘,但早上一碗泡饭,饭店早成为肚子的“麦加”,要赶紧去朝圣一番了。哪知在买饭的时候,摸遍口袋,就是翻不出一张粮票。不行!直截了当地拒绝,售票员没有一点歉疚的表情,我只好怏怏退出。跌跌撞撞又碰了三四处壁,全都没有通融的余地。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位相貌有点类似于观音菩萨的饭店阿姨在要紧关头给我指点了迷津。街衢转过街衢,弄堂穿越弄堂,一直到脚软萧条、眼冒金星时,才终于找到了那爿吃饭不要粮票的“黑市”饭店。《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我倒认为黑有黑的用处。
不过粮票钤在我硬盘中的印记,这还不是刻骨铭心的经历。
40多年前的“文革”后期,全国城乡到处刮“红色台风”,也就是造反派半夜三更三五成群到别人家里去搜查抄家。我们家是农村的居民户,父亲和两个哥哥在外地工作,家里就母亲、我和三哥三个人。户口本上,我家的成份是贫民,完全与专政对象无关。可能是我家外表的生存条件相对于村里其他家庭要好一些的缘故吧,村里的造反派总会隔三差五地来找我们的麻烦。其实我们家的生活来源,也就是父亲每月从邮局寄回的20元生活费,生活质量还比不上殷实的农户呢!尤其口粮,就靠发下来的粮票到镇上的粮站买米,常常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当时口粮奇缺,那些调度不好或者春节急需用钱卖掉了部分口粮的邻居,就会在春花没有登场、存粮亦已告罄的困境下,向我家来借十斤五斤的大米。母亲知道生计之艰,能帮则帮。只是这样一来,我家的口粮就更加勉为其难了。好在当时在外修铁路的二哥口粮定量高,不时能积攒几斤寄回家来,以解无米之炊。记得每次用挑毛线的竹针仔细地挑开挂号信封,展读来信,数着几张全国粮票的时候,母亲就会满脸写意,陶醉与满足的神态,感染得我们也忘乎了所以。出于好奇,我大手大脚地抢过来看,把粮票攥成了皱巴巴的一团。母亲脸色陡变,撕破了叫你饿肚皮!一把又夺了回去。
有一次,就在收到粮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划破皎洁的月色,四五个公社和大队的造反派干部走进我家,说是刮“红色台风”,要查一查有没有未经报告的客人,有没有反动的书籍,有没有不满现实的书信。无奈的母亲只能眼看着这帮子人撬箱子,拉抽屉,开橱门。半个多小时的翻箱倒柜,半个多小时的隐私窥探,半个多小时的上下折腾。最后,实在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只好悻悻然空手离去,理亏到连告别的话都有些语无伦次。
这伙人走后,惊魂甫定,还未等我再睡去,母亲就走到我床前,一把掀掉棉被,问我是不是把夹在家庭账簿里面的10斤全国粮票拿走了。我一脸惘然,觳觫着回答没有。三哥则说黄昏头母亲记账时还看见过。当我们兄弟的清白被证实后,一种不祥的感觉霎时袭向母亲。对,对,刚才那个女的,曾经在放记账簿的抽屉里面翻动了很长的时间。啊、啊!她拿走了十斤粮票!母亲的猜想似乎被证实了。这时,从来文静的她,变得十分愠怒。先是低声自语:叫我们怎么过,下个月怎么办?继之高声叫骂拿走粮票的女人,最后则嚎啕大哭,披上大襟褂子,准备追出去要回粮票。母亲平时经常教育我们兄弟几个:男要有刚强,女要有烈性。那个晚上,估计她准备身体力行。
夜阑人静,我家的哭闹声惊动了隔壁的族叔,他走过来叫三哥拉住母亲,分析说,到底是不是那女的拿走了粮票只是一种猜测,没有十分把握;即使她真的拿了也不会让你搜身,何况旁边的人肯定会护她而不可能帮你,所以万万不能去追。听了族叔鞭辟入里的劝解,一直挣扎着要去讨个说法的母亲总算冷静了下来。第二天,母亲的手臂上满布乌青,人一下好像老去了十岁。从此以后,粮票在我心里就有了山一般的重量。
可也许是因缘际会,我踏入社会以后,竟然一直在粮食部门供职,时间一久审美疲劳,对粮票渐渐变得司空见惯且熟视无睹。粮食放开后,粮票更是老早淡出了我的工作与生活。哪知前些天淘旧货市场,蓦然瞥见了一套全国粮票,久别重逢,既面熟又陌生,既亲切又怨恨。用手抚摸过去,似乎摸到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青涩,再一端详,母亲的音容笑貌也突然浮现在了眼前。想不到,簿簿的粮票竟成了撬动我乡愁的一个支点。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发改委粮管处
|